
肇庆国家高新区(原大旺农场)城区。南方日报记者 郑一见 摄

1983年10月26日,南方日报报道了大旺农场宣布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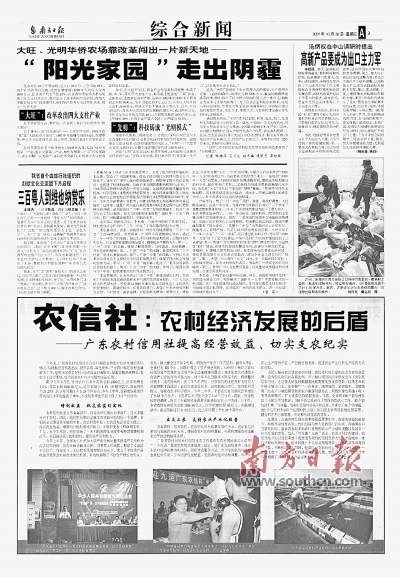
2001年10月30日,南方日报报道华侨农场靠改革创出一片新天地。

2016年12月8日,南方日报报道《广东23个侨场完成升级改制》。
珠海平沙,高耸的烟囱已不见踪影,糖厂旧址“变身”文创园;肇庆大旺,血吸虫病重灾区已华丽转身为国家高新区,成了区域发展的“引擎”;惠州潼侨,归侨们搬进了花园小区,腾出来的空间正在孵化高端产业……这些地方,过去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广东华侨农场。
广东是全国华侨农场数量和安置归难侨(即归侨和难侨)人数最多的省份。改制前,分布于全省14个地级以上市的23个华侨农场,犹如“母亲的臂膀”,将8.4万名归难侨“揽入怀抱”。
然而,在改革开放后,受制于体制等原因,曾经风光的华侨农场却陷入了窘境。
1988年9月3日,南方日报头版刊发消息,宣告广东率先在全国探索实施以体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的“三融入”为导向的华侨农场改革。
这是一场持久战。历经近30年的阵痛与新生,广东华侨农场全部完成升级改制,成为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土、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生力军。
回眸广东华侨农场地区的发展史,中国砥砺前行的步伐清晰可见。
拓荒
8.4万名归难侨到粤
开辟新家园
在肇庆大旺大桥北边,一座雄伟的古铜雕塑——“拓荒牛”吸引了路人的目光,其重心向下、奋力耕耘。
卢丽卿就是这里的“拓荒牛”之一,她是“瞒着家人”跑到大旺的。
1958年,在报纸上看到了华南农垦总局大旺机械化农场(大旺华侨农场前身)的招聘信息,卢丽卿心动了。家人不同意,“任性”的她偷偷拿钥匙打开柜子拿走户口本,然后到居委会登记。没过多久,她惊喜地收到了录取信,离开汕头来到大旺。
处于北江、绥江交汇点的大旺,是广东省面积最大的血吸虫病疫区。建场之初,主要任务是消灭血吸虫病,要治水、灭螺、筑堤、垦荒。大旺没有耕地,几乎全是两米多高的茅草,出门得拿一根竹子绑着白旗再外出,不然很快就看不见人影了。粮食供应也很紧张。在大旺的第一个中秋节,卢丽卿和同伴们忍不住掉眼泪。
经常接触水的卢丽卿,后来患上了急性血吸虫病。有一次头晕如厕时,她不小心掉进了粪坑,第二天才被抢救回来。1960年2月,卢丽卿进入大旺职工医院学习,由此开始了医护生涯,在大旺扎了根。
“华侨农场是在特殊历史时期设立的特殊单位。”广东省委统战部侨务综合处处长吴晓生介绍,1951年12月,全国第一个华侨农场——广东省归国难侨处理委员会农场(珠江华侨农场前身)在万顷沙一带成立。此后,全省各地为安置归侨陆续兴办华侨农场,同时向知识青年敞开了大门。到1978年底,广东共兴办了23个华侨农场(不含当时海南5个华侨农场),安置了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8.4万名归难侨。
1978年10月从越南来到大旺的场景,至今印在苏春福的脑海里:“放眼望去,一片山野都是甘蔗林和香蕉树,房子也破旧不堪。刚抵达的时候,一些人不愿意下车,有的女同胞还哭了起来。”
今年57岁的苏春福坦言,不少人之前住在越南的大城市里,衣食住行等生活条件不错,心理落差自然大,后来也渐渐适应了。
像苏春福一样的海外游子们汇聚到华侨农场,用勤劳的双手,在荒山野岭、海边滩涂上开辟新的家园。
“当时国家和省都把华侨农场职工作为全民所有制农业企业工人来定位和安排,他们的生活水平略高于当地水平。”吴晓生说。
糖、茶、果、奶,成为广东华侨农场产出的“四大件”。平沙华侨农场的平沙糖厂、华丰方便面厂声名鹊起,“一包糖、一碗面”成了平沙人骄傲的资本;英红华侨农场生产的红碎茶,荣获国家银质奖和巴黎国际商品奖;杨村华侨农场发展为亚洲最大的柑橘生产基地;光明华侨农场生产的鲜牛奶,曾占香港市场销售量50%以上。
掉队
“不政不企”陷入窘境
“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啰喂,甜蜜的歌儿甜蜜的歌儿飞满天啰喂,工业农业手挽手齐向前啰喂,我们的明天我们的明天比呀比蜜甜啰。”1979年,取景于平沙糖厂的电影《甜蜜的事业》正式上映,构成了那个年代农场青年的集体回忆。
就在那一年,吴育生跟随家人从越南广宁辗转来到平沙华侨农场。40年弹指一挥间,吴育生种过甘蔗、进过化肥厂,如今是平沙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理事长。
他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春风”记忆犹新:“大锅饭”不再有,包产到户。“改革后,只要肯劳动,把产量、质量搞上去了,家庭收入就高。我们的生活好了很多。”
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席卷全国,华侨农场周边地区发展起来了;由于管理体制僵化、自然条件落后和相对封闭,曾经令人羡慕的华侨农场后来却掉队了。
华侨农场向何处去?
198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国营华侨农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华侨农场由中央和省侨务部门主管的领导体制改为由地方人民政府领导的改革发展方向,拉开了华侨农场改革发展的序幕。
从“七五”至“九五”期间,国家每年安排基建投资3800万元、事业费5000万元,支持华侨农场发展。
“为进一步将华侨农场经济搞活,最近省政府作出决定,将平沙、红旗、珠江、大旺、迳口、光明、杨村、潼湖等华侨农场,下放给所在市管理。下放后的华侨农场,继续享受国家对华侨农场的免税及其他优惠政策。”1988年9月3日,南方日报头版刊发消息,宣告广东率先在全国探索实施了以体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的“三融入”为导向的华侨农场改革。
1990年、1993年和1995年,珠海、深圳和江门市分别成立华侨农场管理区、街道办事处和镇级建制。
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带来了一些起色,但几十年积聚下来的问题,难以一蹴而就。
“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统负盈亏;改革开放后,农场自负盈亏,矛盾就凸显了。”原大旺华侨农场场长、原肇庆大旺综合经济开发区区长张兆熊将原因归结为——“体制不顺、机制不活、所有制单一”。
他说,农场既是安置归难侨的事业性基地,又是进行经济生产的企业实体,集社会性、全民性、企业性、侨民性为一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包含了学校、公安、医院等机构,日常开支大、部门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有人还用“不工不农、不城不乡、不政不企”来形容华侨农场的尴尬。
当时有领导批评大旺招商不积极,张兆熊开玩笑地说:“我招商收上来的税交给了地方,但社会负担增加了,都要农场承担。这样招商招商,越招越伤。”
对于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华侨农场如同烫手山芋“接不住”,发不出工资、买不了社保等情况频出。此外,华侨农场经营自主权加大,投资失误、负债危机等随之而来。
有统计显示:2003年左右,全省华侨农场归难侨居住危房面积竟高达37.3万平方米,占归难侨住房面积的40%;23个华侨农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债务“包袱”,少则一两千万,多则三四亿元。
“华侨农场往昔的辉煌,得益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华侨农场的体制优势;华侨农场后来的发展瓶颈和困难,主要原因在于体制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势在必行。”吴晓生一言以蔽之。
奋进
从“包袱”变为“引擎”
舒适的电梯楼宇、先进的智能工厂、齐全的学校医院……很多归难侨不会想到,陷入低谷的华侨农场会发展为今天这个样子。“环境一直在变。海外的亲戚回来都说认不出来了。”湛江奋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前身为奋勇华侨农场)的印尼归侨陈顺雄感慨万千。
这一切,来之不易。
2007年3月,新一轮华侨农场改革发展的号角正式吹响。吴晓生记得,为从根本上加快推动华侨农场改革发展,在总结广东“三融入”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关于推进华侨农场改革和发展的意见》出台,提出了全面实现“三融入”的目标。
随后,广东也将新一轮华侨农场改革发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印发《广东省推进华侨农场改革和发展实施方案》,明确了2015年华侨农场要彻底告别旧有的管理体制,与所在地实现同地同城同步可持续发展。
广东省委统战部侨务综合处副处长吴功奖参加过多年华侨农场工作。那些年,他和发改、财政、社保、国土等多部门的同事,几乎跑遍了全省的华侨农场,协调推进完善社保体系、危旧房改造、债务处理、土地确权、招商引资等事项。
各方助力,让广东华侨农场地区迈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三融入”挺进深水区,“三化”开启加速度:
工业化“你追我赶”。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以来,凭借土地资源优势和产业扶持政策,全省华侨农场地区共引进工业项目超过1000个,投资总额超过700亿元,金属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化工医药、游艇制造、物流、农业、旅游等特色产业集群初具规模。肇庆高新区(大旺华侨农场)成为全国第一个在侨场区域建立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湛江市奋勇经济区被授予“中国—东盟经济开发区”,过去的“包袱”已进化为今天的“引擎”。
城镇化步伐加快。华侨农场地区全部通高速公路,基本实现村村通水泥路,“出行难”“饮水难”“用电难”“就医难”“就学难”等问题迎刃而解。在惠州潼侨镇(前身为潼湖华侨农场),印尼归侨黄瑞丰一家只出了1万多元,就从年久失修的泥瓦房搬进了窗明几净的高层公寓,面积大了不止一倍。
农业产业化持续发力。英红九号、珠江绿色有机蔬菜、北极罗非鱼、陆丰优质水果等农产品打响了品牌,远销各地。在平沙,吴育生还将休闲观光旅游与农业融合起来,延长了产业链。
2015年7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省政府关于华侨农场改革发展情况专项工作报告,肯定了23个侨场基本实现“三融入”目标。
经过8年努力,广东华侨农场“脱胎换骨”,形成了设镇街、并镇、设管理(经济)区、设开发区、改制企业等五种模式,历史遗留问题基本解决,学校、医院、公安等社会事务纳入地方政府归口管理,归难侨及职工群众生产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广东华侨农场地区以‘三融入’为主线,融入了改革开放的热潮,与国家和地方共同成长。”吴晓生说,如今有些华侨农场地区还被纳入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空港经济区、国家或省市高新区,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方面,可以进一步发挥侨力资源、国有土地资源和区位交通等优势,为广东奋力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当好“两个重要窗口”作出新的贡献。
年轻时,第一代归难侨苏春福一心想逃离大旺,现在他已经舍不得走。2年半前,归侨子弟唐德勤回到大旺工作。见证着家乡的变化,他既自豪又充满干劲。这样的故事,在广东华侨农场地区屡见不鲜……
见证者说
暨南大学教授、《广东华侨史》主编张应龙:
华侨农场的两样“传家宝”不能丢
深耕华侨华人研究将近40载,暨南大学教授、《广东华侨史》主编张应龙的足迹遍及全省过半华侨农场。
提到华侨农场的历史,他娓娓道来:对于归难侨,早期国家是采取按照籍贯分散安置的办法,后来发现效果不如预期,于是改为集中安置为主、分散安置为辅。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从印尼、越南等24个国家接收了近35万归难侨,并在7个省区通过兴办农场、林场和农垦等方式,使他们成为新中国建设的一分子。
改革开放前,尽管国家经济建设还没有大的发展,物质匮乏,仍给予华侨农场人员国家全民职工身份,实行政企合一、部门领导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人财物、产供销由侨务部门直接领导。当时农场的待遇让周边群众十分羡慕,不少人盼着能进场工作。
然而,由于安置时间紧,选址和布局不甚合理,多数华侨农场所处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较差,加之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等靠要”观念、人才缺乏等方面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华侨农场发展滞后。
张应龙调研过广东多个华侨农场地区,对当地的痛点、归难侨们的心声深有感触。“传统的农场产业单一,靠天吃饭,不确定因素多,抗风险能力弱,要跟上时代发展,最关键的是推进经济的全面转型升级。但有的农场盲目投资,导致项目烂尾;有的农场区位不好,也跟风发展。实际上应该聚焦主业,不能盲目多元化。”
在上级下大力气优化顶层设计、强化配套保障、逐步理顺机制后,全省华侨农场“轻装上阵”,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开始找准了经济发展的方向,不再只是“农场”了。
张应龙早期走访迳口华侨农场时,那里还是穷乡僻壤,可以说是“佛山的西伯利亚”。时隔几年,他再度到访,看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盖了很多新房,还有不少企业落户,当地领导也雄心勃勃。
“历史地看,华侨农场真正纳入地方发展的一盘棋,需要一个过程。”他注意到,在管理体制转换过程中,在保留农场完整性的基础上设立镇街或开发区的地方,发展相对顺利;有些被合并的农场,则面临更多磨合的问题,发展起来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成本。
“几十年来,广东华侨农场地区经历了不少波折和考验,但最终达到了改革目标,在全国形成了示范。归难侨和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当地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张应龙说,在新时代,华侨农场的两样“传家宝”仍然不能丢,一是艰苦奋斗的拓荒精神,二是丰富多彩的华侨文化,要不断传承弘扬。
南方日报记者 胡良光 林亚茗 马喜生 董谦君
实习生 陈舒婷 通讯员 梁爱玲 李建军 阳涛